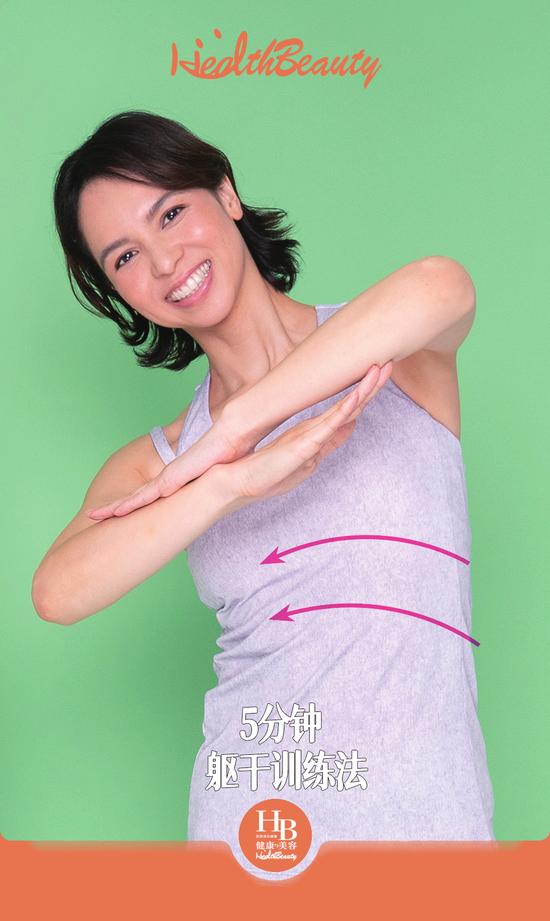記者蕭採薇/台北報導
演藝圈大姐大「寬姐」邱瓈寬母親1日因肺炎病逝,享耆壽93歲,追思會場開放至14日,不少娛樂圈好友都現身陪伴。「小豬」羅志祥在關閉前最後半小時前來慰問,經紀人透露,他這幾天在西班牙有拍攝工作,上午還有會議,一有空檔就趕過來,「抱歉來得比較晚。」

接連幾天好友們都到追思會場,陪伴寬姐度過喪母之痛。追思會場於14日晚間6點關閉,羅志祥約在5點20分趕到,大約待了15分鐘。據悉,他因為16日又要去海外工作,無法參加邱瓈寬母親的告別式,特意抽空前來致意。

羅志祥離開時低調不願受訪,緊雙手合十表示,快速步上車,邊走邊說:「希望她好好休息,謝謝。」14日為靈堂開放最後一日,男團Energy成員牛奶(葉乃文)、言承旭、王菲經紀人陳家瑛、洪曉蕾、吳敏、余天、李亞萍、瘦子、張震嶽、寇乃馨、黃國倫等人陸續現身陪伴。
標題:羅志祥飛回台北「趕到邱母靈堂」見寬姐! 雙手合十:希望她好好休息
鄭重聲明: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,轉載文章僅為傳播信息之目的,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,如有侵權行為,請第一時間聯絡我們修改或刪除,多謝。